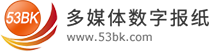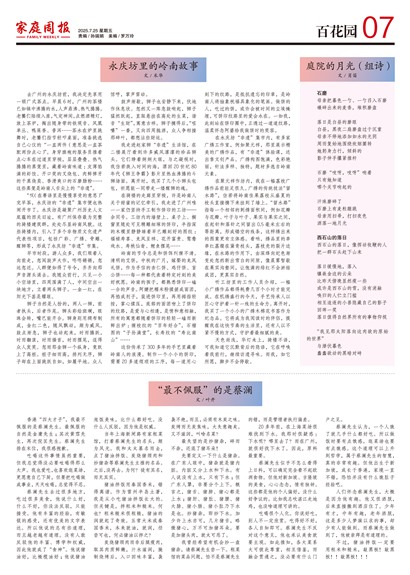文/禾华
去广州的永庆坊前,我决定先享用一顿广式茶点。早晨6时,广州的茶楼已如锅中沸腾的水,人声鼎沸、热气腾腾。老饕们陆续入座,气定神闲,点燃酒精灯,放上茶炉,掏出随身带的铁观音、凤凰单丛、鸭屎香、普洱……茶水在炉里跳舞时,老饕们指节轻叩桌面,准备挑选自己心仪的“一盅两件(意思是一盅茶配两份点心)”。身穿旗袍的服务员推着点心车在过道里穿梭,层层叠叠、热气腾腾的蒸笼里,藏着岭南味道:皮薄馅满的虾饺、开口笑的叉烧包、肉鲜弹牙的干蒸烧卖、香滑爽口的石磨肠粉……这些蒸笼是岭南人舌尖上的“非遗”。
“叹(在粤语里是慢慢享受的意思)”完早茶,永庆坊的“非遗”集市便也热闹开市了。永庆坊是凝聚广州历史人文底蕴的西关旧址,有广州保存最为完整的骑楼建筑群,处处尽显岭南风貌。这些骑楼内,引入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包括广彩、广绣、骨雕、醒狮等,形成了永庆坊“非遗”市集。
早市时段,游人众多,我们顺着人向前走,忽闻鼓声大作,咚咚锵锵,忽远忽近。人群便如得了号令,齐齐向那声音源头涌去。我随众前行,只见一小小空场里,四周围满了人,中间空出一块地方,立着两头狮子。一金一红,在阳光下甚是耀眼。
狮子当然是人扮的,两人一狮,前者执头,后者作尾。狮头彩绘斑斓,眼珠会转,嘴巴能开合。狮身则用绸布制成,金红二色,随风飘动,颇为威风。鼓点渐急,狮子也动起来,时而腾跃,时而翻滚,时而搔首,时而摆尾,逗得众人发笑。忽而那金狮一个纵身,竟跃上了高桩。桩子细而高,排列无序,狮子却在上面跳跃自如,如履平地。众人惊呼,掌声雷动。
鼓声渐歇,狮子也安静下来,伏地作休息状。忽然又一阵急鼓响起,狮子猛然跃起,直取悬挂在高处的生菜,谐音“生财”,寓意吉祥。狮子摘得后,“咀嚼”一番,又向四周抛洒,众人争相接那碎叶,都想沾些财运。
我走进赵家狮“非遗”生活馆,在二楼展厅看到许多威风凛凛的珍品狮头。它们睁着炯炯大眼,与之凝视时,我仿若跌入时间的海,漂回20世纪80年代《狮王争霸》影片里热血沸腾的斗狮场面。离开时,我买了几个小狮头包包,祈愿能一同带走一缕醒狮的魂。
在骑楼的走廊里穿梭,许是岭南人关于甜蜜的记忆牵引,我走进了广州唯一一家仍坚持手工制作饼印的工坊——余同号。工坊内的墙壁上、桌子上、橱窗里随处可见精雕细琢的饼印,半指深的木模里静静睡着早已雕刻好的图纹:福禄寿喜、龙凤呈祥、花开富贵、鸳鸯戏水、寿桃仙翁、鲤鱼摆尾……
岭南的节令总是和饼饵纠缠不清。清明的艾饼,中秋的广月,嫁娶的龙凤礼饼,作为手信的杏仁饼、鸡仔饼、盲公饼……每一种都代表着特定时刻的美好祝愿。岭南的孩子,都熟悉饼印一磕一合的声音。阿嬷把糯米粉揉搓成面团,再掐成剂子,装进饼印里,再用拇指轻按,掌心揉压,底部的面团吻上了饼印的纹路,是爱与心相逢,是情和意相融,所有的寓意都随着饼印的轻轻一磕而新鲜出炉:缠枝纹的“百年好合”,石榴图的“子孙满堂”,长寿纹的“寿比南山”……
这份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里藏着岭南人的浪漫。制作一个小小的饼印,需要20多道烦琐的工序,每一道用心刻下的纹路,是抵抗遗忘的印章,是岭南人将抽象祝福具象化的笔画。做饼的人,吃过的饼,或许会被时间的尘埃掩埋,可饼印纹路里的爱会永在。一如我,此刻站在饼印圈中,正透过一道道纹路,温柔怀念阿婆给我做饼时的笑容。
在永庆坊“非遗”集市内,有多家广绣工作室,例如聚元祥,那里展示精美的广绣作品,有“非遗”体验课,还出售文创产品。广绣构图饱满,色彩艳丽,针法多样、独特,题材多选自岭南元素。
在聚元祥作坊内,我在一幅荔枝广绣作品前驻足很久。广绣的传统技法“留水路”,仿若将岭南佳果荔枝从盛夏的枝头直接摘下来挂到了墙上。“留水路”指每一个相邻的刺绣面积间,例如花瓣与花瓣、叶子与叶子、果实与果实之间,在起针和落针之间留出0.5毫米左右的等距离,形成镂空的线条,这样绣出来的图案更有立体感。看呐,绣品里的串串红荔缀在黛青枝头,荔枝壳的裂片边缘,在水路的作用下,由深绛向妃色渐变处忽然断出雪白的间隙,像晨雾暂歇在果实沟壑间,让饱满的绯红不会淤结成团,更真实自然。
听工坊里的工作人员介绍,一幅小广绣作品都得耗费几百个小时才能完成。在机绣盛行的今天,手艺传承人以匠心守护着一针一线的生命力。离开时,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广绣木棉花书签作为纪念品。它将成为我阅读时的伴侣,提醒我在这快节奏的生活里,还有人以不紧不慢的方式,守护着最细腻的美。
天色尚浅,华灯未上,骑楼不语,可我知道它沉默背后的隐语,它在呼唤着我前行,继续访遗寻味。而我,如它所愿,脚步不会停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