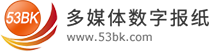文/叶艳莉
伊阙连冈,东西横亘,水上编木桥之。渡而西,崖更危耸。一山皆劈为崖,满崖镌佛其上。大洞数十,高皆数十丈。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顶,顶俱刊小洞,洞俱刊佛其内。虽尺寸之肤,无不满者,望之不可数计。
这是400多年前,大旅行家徐霞客站在龙门石窟前看到的壮观景象。伊阙,即龙门。这里东西两山对峙,伊水从中流过,望之若阙,所以古称“伊阙”。龙门石窟的“满”“高”“不可数计”,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2000年11月,龙门石窟以3个“最”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委们折腰,用最快的速度通过审议。他们是这么评价的:“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,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。这些翔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,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。”“最具规模”“最为优秀”“最高峰”,谁能抵挡这“最”魅力?于是,龙门石窟没有任何异议地走入了世界遗产的大家庭。
“最具规模”,这规模该有多大?伊水将两岸的香山和龙门山削成天然画轴,2345个窟龛、近11万尊佛像、2800多块题记碑刻次第绽放,在崖壁上写下中国艺术最磅礴的章回。
章回的第一笔,和北魏孝文帝有关。北魏太和十七年(493年),孝文帝以“南伐”之名启动了迁都计划。向南,向南从塞上平城(今山西大同)到中原腹地洛阳,这一豪举,不仅是首都的迁移,也是对汉文化的渴望,更是民族融合的启幕。在迁都的同时,龙门被选中营造皇家洞窟。中国营造石窟的舞台,从山西云冈转移到河南龙门。
凿山为佛,实乃凿胡汉之界。云冈石窟的雄浑粗犷,化作龙门石窟的“秀骨清像”——佛陀眉眼里,有了南朝士人的风姿。削方铲平的鼻梁变得圆润,雄健的身姿变得清秀,严峻的表情变得和蔼,草原与中原,在一颦一笑间达成了和解。
北魏匠人凿下第一锤后,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隋、唐等朝代,斧凿不歇,如蜜蜂筑巢般把石窟密不透风地镶嵌在南北绵延一公里的伊水河畔。远远望去,龛窟依稀虚化为文字,两岸山崖成了一部摊开的线装书,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,被一一记录在册。
正如伊水汤汤,从未停止搬运岩石,中国何曾停止吸收外来文化?一条“石窟走廊”,见证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,也见证了世界文化的交融汇聚。古阳洞的连珠纹图案,蕴含着萨珊波斯装饰美术的因素。宾阳中洞门券拱下的柱头,分明带着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的痕迹。驻足于窟檐的金翅鸟,昭示着与西域文化的互动。中原乐器横笛、阮、排箫、笙与西域乐器腰鼓、箜篌、筚篥、琵琶一起出现在乐队里,合奏着文明的交响。天竺人、新罗人、吐火罗人和康国人皆在此造像,成为对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生动翻译。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面对历史风云的从容姿态。海纳百川是中华民族对话世界文明的东方智慧。
人们在龙门石窟留下了自己的笔迹,唐代,无疑是其中最绚烂的一笔。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,北魏洞窟约占30%,唐代占60%,其他朝代仅占10%左右。而卢舍那大佛的微笑,无疑是唐代最辉煌的一笔。
唐上元二年(675年),龙门迎来了大唐帝国最尊贵的人——皇后武则天。她是来参加卢舍那大佛竣工仪式的。为了开凿大佛,她“助脂粉钱二万贯”。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来说,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,但其示范作用巨大。工程顺利完成,大佛向世人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姿容:通高17.14米,头高4米,耳长近2米,身披通肩袈裟,发似波浪,眉如新月,目若秋水,面容丰满,微微上翘的嘴角停泊着一抹恬静的微笑。站在大佛脚下仰望,目光恰同微微俯视的双眸交会,那抹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笑容瞬间让人恍惚了心神,时间仿佛停止,“东方蒙娜丽莎”的赞美也成为语拙后的无奈表达。传说大佛的面相,正是以武则天为原型。真相或许已不可得知,但盛唐以“方额广颐”为美的时代风尚留给大佛的深刻印记,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。
工匠的巧手,让岩石生出丝绸的柔软。大佛周边,二弟子温顺虔诚,二菩萨华贵端庄,二天王魁梧威猛,二力士气势逼人。整组雕像众星拱月,对中心的卢舍那大佛形成簇拥态势,烘托出大佛的至高无上。这组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,无论造型还是布局,都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,堪称唐代雕刻艺术的精华,也成为唐朝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。
面对这样的艺术杰作,谁能不为之动容呢?1936年初夏,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夫妇的信中,如此表达自己的震撼:
我正坐在龙门最大的露天石窟下面,九尊最大的雕像姿态各不相同,面容祥和,体态灵动,或坐或立地凝视着我。(我也仰望着他们!)
……
此刻我侧身背略向左,面向众佛,仰望鬼斧神工奉上的整座开山佛龛。我的思绪随着脚下的伊河潺潺流动,落日余晖在人与佛间穿梭闪烁,报春花和三叶草伴着风弥漫着初夏的草香,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引我坠入神秘的静潭,说它是宗教,但(那美)却比任何宗教都更有魅力和浪漫。
美,具有穿越的力量。它穿过会昌灭佛的劫火、金元铁骑的箭镞、民国盗匪的钢钎,在无数人的凝视中永恒。石壁上永不褪色的伊阙长歌,告诉人们:人类所有文明的孤岛,终将在美的潮汐中连成大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