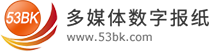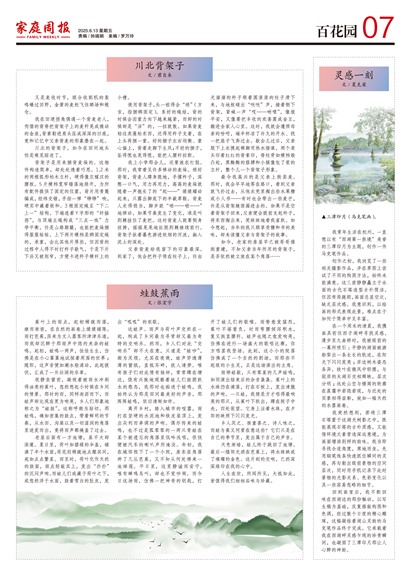文/张宏宇
蕉叶上的雨点,起初稀疏而落,继而渐密,在自然的画卷上缓缓铺陈。雨打芭蕉,历来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,而我却沉醉于那雨声中隐约夹杂的蛙鸣。起初,蛙鸣一两声,怯怯生生,仿佛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周围的世界;随即,这声音便如潮水般涌动,此起彼伏,汇成了一片壮阔的乐章。
我静坐窗前,凝视着被雨水冲刷得油亮的蕉叶,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间的情景。那时的雨,同样淅沥而下,而蛙声却比现在更为响亮,乡人们形象地称之为“蛙鼓”,这称呼颇为贴切。那蛙鸣,确如密集的鼓点,带着鲜明的节奏,从水田、沟渠以及一切湿润的角落里迸发而出,竟将雨声都掩盖了过去。
老屋后面有一方池塘,虽不大却深邃。夏日里,荷叶如碧绿的伞盖,铺满了半个水面,荷花则稀疏地点缀其间,宛如点点繁星。雨至时,荷叶化作天然的鼓面,雨点轻敲其上,发出“扑扑”的沉闷声响。而蛙儿们或藏于荷叶之下,或悠然浮于水面,鼓着雪白的肚皮,发出“呱呱”的欢歌。
这蛙声、雨声与荷叶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乡间最为寻常却又最为奇特的交响乐。然而,乡人们对此“交响乐”却不大在意,只道是“蛙吵”,颇为厌烦。尤其在夜晚,蛙声穿透薄薄的窗纸,直抵耳畔,扰人清梦。唯有孩子们对此情有独钟,常常蹲在塘边,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蛙儿们鼓腮跃水的憨态,我那时也痴迷于蛙鸣,我始终认为那是田间最美好的声音,那阵阵蛙鸣,依旧清晰如昨。
离开乡村,踏入城市的喧嚣,雨打在坚硬的水泥地和铁皮屋顶上,发出尖利而单调的声响。偶尔传来的蛙鸣,也不过是孤零零的一两只青蛙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低吟浅唱,很快便被汽车的喇叭声所淹没。年初,我在城郊租下了一个小院,房东在角落种了几丛芭蕉,又不知从何处移来一池睡莲。平日里,这里静谧而安宁,唯有蝉鸣鸟叫,却也不觉吵闹。而今日这场雨,仿佛一把神奇的钥匙,打开了蛙儿们的歌喉。雨势愈发猛烈,蕉叶不堪重负,时而弯腰倾泻积水,复又挺直腰杆。蛙声也随之愈发响亮,仿佛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歌唱比赛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此刻,这小小的院落仿佛成了一个自然的剧场,而那些不起眼的小生灵,正是这场演出的主角。
雨停蛙歇,只有零星的几声蛙鸣,如同演出结束后的余音袅袅。蕉叶上的水珠仍在滴落,打在石板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只蛙,我猜是方才唱得最响亮的那只,从蕉叶下跃出,蹲在院子中央,四处张望。它身上沾着水珠,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。
乡人厌之、孩童喜之、诗人咏之,而蛙与蕉又何曾在意这些?它们只是在自己的季节里,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天色渐暗,蛙儿终于跳回了池塘。最后一缕阳光洒在芭蕉上,将水珠映成了璀璨的金色。这片刻的交响,已然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人生在世,所闻所见,大抵如此,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珍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