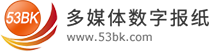文/陆锋
江南的节气总在衣襟间游走。春衫未收,夏衣已晾上竹竿。
巷子口卖油墩子的阿婆还裹着暗红毛衣,袖口磨得起了球,倒像是给油锅里翻腾的面团添了把柴火。她说这毛线是30年前女儿出嫁前织的,“春脖子长,得让毛线在骨头上焐出油光”。穿堂风掠过时,阿婆总要拢一拢衣襟,她身边等早点的年轻人穿着短袖,却把脖颈仰得更高,让风灌进领口,仿佛这样就能提前饮到夏天的梅子汤似的。油锅腾起的热气裹着毛衣的羊毛味,和年轻人短袖上的皂角香在空中打了个旋,恰似春秋两季在云絮里悄悄换了岗。
巷尾的老裁缝被衣裳里的春秋惊动。他戴着铜顶针穿针引线:“江南的节气是活的。春寒爱往人骨缝里钻,得用斜纹布锁边;暑气爱贴皮肉游,需拿提花绸透气。”说话间银剪游走,裁下几片海棠影,正落在客人新制的藕荷色旗袍上。针脚里的智慧,原是世代相传的。竹尺量过三代的腰身,粉线划过百年的光阴,那些藏在立领里的盘扣,总要留两分分量——不是为着发福,是给江南时晴时雨的脾气留余地。
我常在桥头石阶上坐着看衣裳河——穿羊绒开衫的妇人拎着菜篮,与穿真丝衬衫的少妇擦肩而过,衣袂相触时交换了冷暖。蓝印花布包裹的茭白撞上透明塑料袋里的冰镇杨梅,倒像两个季节在菜篮里握手言和。骑单车的少年将外套绑在车头,猎猎作响如招展的旗。衣裳们追着车铃跑,把整条街的节气搅得微微摇晃。车筐里斜插的栀子花沾了风衣的烟草味,校服衣角蹭着公文包的牛皮纹路,都是光阴在布料上盖的邮戳。
起风了,满街的衣袖裙裾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飘。
每件衣裳都揣着半阕诗,婆娑处,尽是未写完的江南韵脚——穿碎花睡裙的妇人推开雕花窗,晾衣竿挑起的裙裾便成了押韵的诗行;晨跑的年轻人耳机线缠着运动服拉链,脚步踏出“阳平”的节奏;夜归的醉汉把领带系在额头,摇摇晃晃地踩着“去声”的拍子。整条街的平仄都写在衣褶里,风一吹,平平仄仄便淌进河水,惊醒了眠在桥洞的半个月亮……
衣裳河仍在流淌,今朝的罗裳已浣成往事的纱,重重叠叠的衣影缝缀成了连绵不绝的江南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