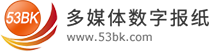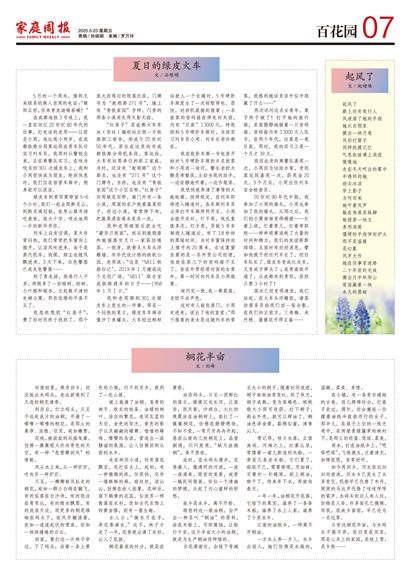文/刘峰
时值初夏,乘舟回乡。还没抵达水码头,老远就嗅到了久违的桐花清香。
到岸后,伫立码头,只见不远处成片的油桐,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桐花,是那么的素净、淡雅、空灵,宛如嫩雪。
花枝,被寂寂的风摇曳着,仿佛一簇簇焰火扑向青色的天空,有一种“急雪舞回风”的情致。
风从水上来,从一种茫茫,吹向另一种茫茫。
只见,一瓣瓣被风扯走的桐花,宛如一群小白鸽在翻飞。有的坠落在白沙洲,有的隐没在青苇丛,有的随水飘零,有的流浪天边。而更多的桐花堆砌在码头下,在风中翻涌着,犹如一道道起伏的雪浪,恰如一抹抹缱绻的白云。
回家,要打这一片林子穿过。下了码头,沿着一条土黄色的小路,行不到百步,就到了一处山坡。
坡上栽满了油桐。苍青的树干、铁灰的枝条、油绿的树叶、洁白的繁花,连同瓦蓝的天空、金色的阳光、紫色的影子以及翩翩的蝶舞、嗡嗡的蜂鸣、嘤嘤的鸟语,营造出一派静谧的氛围,让人仿佛回到从前的水乡。
走在林间小道,时有落花飘至。花打在头上,起初,有一种微微的疼,但很快,化作一缕酥酥的麻,甜丝丝,凉沁沁,仿佛在给人按摩。花碎后,留下鹅黄的花蕊,似流苏一样散落在衣衫,犹如古代衣饰上的黄金缕,别有一番生趣。
古人云: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”这不,林子才走了一半,花香就沾满了衣衫,沁入了肌肤。
桐花最美的时分,就是在黄昏。
站在码头,只见一团鲜红的落日,缓缓沉向长河。江面赤,西天紫,沙洲白。火红的晚霞涂在油桐树上,染红了一簇簇桐花,仿佛在静静燃烧。不知不觉,一弯月牙冉冉升起,悬在山坡的几枝桐花上,晶莹剔透,闪闪发亮。“缺月挂疏桐”,美不胜收。
此时,在水码头漫步,花香袭人,像透明的河流,一波一波涌来。眼前的美景,宛若一幅民间版画,恰似一个清幽的梦境,泛起了内心蜜样的轻愁。
故乡是水乡,离不开船。
眼前的这一坡油桐,会产出一种名叫“桐油”的原料,涂在木船上,可防腐蚀,让船行千里。这片半亩大小的油桐,就是为生产桐油而种植的。
当花凋谢后,会结下青豌豆大小的桐子。随着时间流逝,桐子渐渐由青变红。到了秋天,桐子成熟,变为深褐色、核桃般大小即可收获。打下桐子,剥去外壳,就可以榨油了。桐油色泽金黄,黏稠似蜜,清香沁人。
常记得,秋日水落,正值渔闲。河滩之上,红蓼丛里,常摆着一溜儿新造的木船,一旁是几条老木船。它们累了,斑驳不已,需要修理,用细麻、石膏补一补缝隙,刷上桐油,晒干了,待来年下水,再驶向春天。
一年一年,油桐花开花落。它结下的果实,滋养了一条条木船,滋养了水上人家,滋养了十里水乡。
江南的油纸伞,一样离不开桐油。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水乡出丽人,她们仿佛是水做的,温婉、柔美、多情。
在小镇,有一条青石铺砌的古巷。雨儿绵绵时分,打巷子走过,偶尔,你会邂逅一位撑着油纸伞款款而行的女子。那伞儿,在巷子上空的一线光亮中,在两壁青绿藤萝的映衬下,是那么的轻盈、俏丽、柔美。
雨水,打在油纸伞上,“吧嗒吧嗒”,飞珠溅玉,泛着清光,如弹琵琶,非常好听。
如今再回乡,河水依旧汩汩向前流,但水乡已发生了太多变化。机船早已代替了木舟,突突的马达声代替了吱吱呀呀的桨声。水码头依旧人来人往,但物是人非,许多面孔已模糊。而我,在故乡面前,早已沦为一名过客。
只有这桐花半亩,与水码头不离不弃,依旧笑在风里。那是心灵上的家园,是枝上雪,是乡愁……